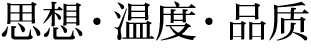我在北海公园送过水
北京西城报
2025-07-11 11:01

007
2003年春节过后,我辞别还没过百天的女儿,怀揣着对大城市的憧憬来到北京打工。我找到了一份送桶装水的工作,老板给配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送一桶水提成1元。北海公园那时候每周订10桶水,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已然是大客户,每次去送水,我都不敢有丝毫怠慢。
初次踏入北海公园,映入眼帘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岸边垂柳依依,随风轻轻摇曳。在东门的门卫室前,我见到了张叔——一位五十多岁、来自房山的和蔼大叔。他皮肤黝黑,眼角布满了岁月的痕迹,笑起来让人倍感亲切。每次登记进入公园,他总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闲暇时,张叔会和我聊起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自己曾去陕北插过队,和作家史铁生插队的地方不远。得知我喜欢在业余时间读文学类书籍,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没过几天,他便从家里带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送给我。“这书好,你好好看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从那以后,每当结束一天的劳累,我都会在地下室的小床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沉浸在史铁生的文字世界里,感受着他对生命的思考与感悟。张叔的这份礼物,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也让我们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成了忘年交。
2004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北海公园送水。和张叔打过招呼后,心急火燎地搬着水桶往行政楼跑去,匆忙间竟忘记锁上三轮车。等我送完水下来,原本停放三轮车的地方已空空如也。那一刻,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这辆三轮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我工作的工具,更是我在北京谋生的希望。要是丢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老板交代,又拿什么去继续这份工作。
我发疯似的沿着湖堤飞奔,眼睛盯着四周,希望能看到三轮车的踪影。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喉咙也变得沙哑,可始终不见三轮车的影子。绝望、无助的情绪在我心中翻涌。
我失魂落魄地跑到东门,见到张叔,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张叔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有个毛贼慌慌张张骑着你的车就要出门,被我一眼认出来了,车在门卫室后边呢,那小子已经送派出所了。”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让我悬着的心渐渐落了地。我紧紧握住张叔的双手,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又一句的“谢谢”。那一刻,我对张叔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后来,媳妇把女儿托付给岳父岳母,也来北京打工了。我带着她去看望张叔。张叔热情地带着我们游览北海公园。他像个专业的导游,详细地给我们介绍着公园里的每一处景点,讲述着那些背后的历史故事。那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我们漫步在公园的小道上,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游览结束后,张叔还坚持请我们吃饭,点了好几个硬菜,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几年后,因为一些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老家。临走前,我特意去北海公园和张叔告别。张叔沉默了许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孩子,回去好好干,有机会常回来看看。”我点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不敢回头,生怕多看一眼,就会舍不得离开。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没了张叔的联系方式。算起来,他可能已经八十岁了,和我父亲一般大。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是否还硬朗,是否还会在闲暇时想起曾经那个在北海公园送水的小伙子。每当想起北海公园,张叔那慈眉善目的模样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给予我的帮助和温暖,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始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作者雷焕

初次踏入北海公园,映入眼帘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岸边垂柳依依,随风轻轻摇曳。在东门的门卫室前,我见到了张叔——一位五十多岁、来自房山的和蔼大叔。他皮肤黝黑,眼角布满了岁月的痕迹,笑起来让人倍感亲切。每次登记进入公园,他总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闲暇时,张叔会和我聊起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自己曾去陕北插过队,和作家史铁生插队的地方不远。得知我喜欢在业余时间读文学类书籍,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没过几天,他便从家里带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送给我。“这书好,你好好看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从那以后,每当结束一天的劳累,我都会在地下室的小床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沉浸在史铁生的文字世界里,感受着他对生命的思考与感悟。张叔的这份礼物,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也让我们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成了忘年交。
2004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北海公园送水。和张叔打过招呼后,心急火燎地搬着水桶往行政楼跑去,匆忙间竟忘记锁上三轮车。等我送完水下来,原本停放三轮车的地方已空空如也。那一刻,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这辆三轮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我工作的工具,更是我在北京谋生的希望。要是丢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老板交代,又拿什么去继续这份工作。
我发疯似的沿着湖堤飞奔,眼睛盯着四周,希望能看到三轮车的踪影。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喉咙也变得沙哑,可始终不见三轮车的影子。绝望、无助的情绪在我心中翻涌。
我失魂落魄地跑到东门,见到张叔,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张叔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有个毛贼慌慌张张骑着你的车就要出门,被我一眼认出来了,车在门卫室后边呢,那小子已经送派出所了。”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让我悬着的心渐渐落了地。我紧紧握住张叔的双手,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又一句的“谢谢”。那一刻,我对张叔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后来,媳妇把女儿托付给岳父岳母,也来北京打工了。我带着她去看望张叔。张叔热情地带着我们游览北海公园。他像个专业的导游,详细地给我们介绍着公园里的每一处景点,讲述着那些背后的历史故事。那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我们漫步在公园的小道上,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游览结束后,张叔还坚持请我们吃饭,点了好几个硬菜,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几年后,因为一些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老家。临走前,我特意去北海公园和张叔告别。张叔沉默了许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孩子,回去好好干,有机会常回来看看。”我点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不敢回头,生怕多看一眼,就会舍不得离开。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没了张叔的联系方式。算起来,他可能已经八十岁了,和我父亲一般大。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是否还硬朗,是否还会在闲暇时想起曾经那个在北海公园送水的小伙子。每当想起北海公园,张叔那慈眉善目的模样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给予我的帮助和温暖,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始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作者雷焕




打开APP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