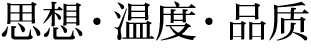护国寺不仅有小吃 曾经也有寺
北京西城报
2025-08-01 11:00

008
从元代赵孟頫笔下的《崇国寺演公碑》,到今日人声鼎沸的护国寺小吃店;从九重殿阁的皇家巨刹,到梅兰芳低回婉转的京剧舞台……短短数百米的护国寺街,折叠了北京七百余年的历史。让我们循着晨钟暮鼓的余韵,穿过烟火与粉墨,去重访这座“活着的博物馆”。
 如今的护国寺街景
如今的护国寺街景
 游客在梅兰芳故居前拍照打卡
游客在梅兰芳故居前拍照打卡
 如今的人民剧场
如今的人民剧场
 护国寺金刚殿作为市级文保单位仅限外部参观
护国寺金刚殿作为市级文保单位仅限外部参观
 护国寺小吃特色必吃榜
护国寺小吃特色必吃榜
 护国寺小吃店铺
护国寺小吃店铺
 如今的金刚殿外景
如今的金刚殿外景
从崇国寺到护国寺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一幅传世作品《崇国寺演公碑》,被赞为“人书俱老,用笔圆润端肃”,是其晚年书碑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碑文内容也是一份重要史料。
《崇国寺演公碑》全称《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立于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由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丹、篆额,记述了护国寺前身崇国寺始创者定演禅师的生平事迹,以及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赐地兴建崇国寺的来龙去脉。这座为后世史书誉为“悉皆完美”的崭新佛寺名曰“崇国寺”,为区别于此前已存在的一座同名寺院,时人呼其为“北崇国寺”或“崇国北寺”。
北崇国寺开创于元代,而崇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清代《日下旧闻考》收录危素的“大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证慧禅师傅戒碑略”中记载了元军攻打金军时“闵忠崇国二寺”俱为兵毁,以及元朝大臣雅克里、耶律楚材等修复两寺的事迹,可知崇国寺在元灭金战争中被毁,嗣后得以重建。而《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赵宋宗室赵子砥《燕云录》记下了靖康之耻时“中书侍郎陈过庭并文武官五十余员”于丁未八月在燕山崇国寺安泊的记录,这意味着崇国寺可能在辽宋时期便已存在。据黄春和先生在《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中考证,隋唐时期幽州城佛寺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可考者达17座,其中便有悯忠寺和金阁寺两座。据《顺天府志》载:“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析津志》中也道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
为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护国寺之名,是逐步演化来的,几乎每修一次,都要改换一次寺名。明宣德四年重建后,由崇国寺改为御赐的大隆善寺,到了明正统四年,重修后又改为崇恩寺。到了33年后的成化八年,由著名的大工匠工部侍郎蒯祥主持重修,赐名大隆善护国寺,这是护国寺其名之始。后经康熙、乾隆、道光历岁重修,护国寺之名未再更改,山门上始终是大隆善护国寺的石额。
护国寺的整体格局,也是逐步形成的。随着逐代的增修,护国寺的纵深越来越夸张,主要是不断增加前端的门户。护国寺天王殿是最早的山门,正统时在其前增建一道山门——金刚殿,到了成化那次重修,又在金刚殿前加了座临街砖石山门,全寺格局才最终形成。
护国寺只门户就有三重之多,三门之后,又有层层递进的三座大殿,而这三门三殿,还只是前院,后院还有一门一殿一坛一楼,由此形成了超长纵深的九进格局,这是元代大寺院的典型特征,前院廊庑围合的特点也是型古而制高,颇有巨刹古风。
值得一提的是前院最后端的千佛殿,这才是最古的殿宇,俗称土坯殿,20世纪30年代寺庙调查时土坯墙坍塌只剩四框,但正是这残存的土坯墙和独特的角石,证明这是一座元代建筑。同时期还有舍利塔、后院门前石狻猊及数通元碑,保存至今的,除石碑外,也只有千佛殿的元代雕花柱础了(一在原址,一在北京钟楼台基东坡道北角)。其余的钟鼓楼、金刚殿、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三大士殿、戒坛以及配殿廊庑都已属明清建筑。
因庙会变得十分热闹
除了以朝廷的香火寺和藏传佛教僧人居住而闻名之外,护国寺更以庙会享誉京城内外。佛寺在古代长期承担着公共空间的角色,同时也是许多地方的文化中心。而建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寺院,不仅在宗教、政治和文化上活跃,又是市民的活动广场与休闲胜地,更承担了十分突出的商业功能,其主要形式之一便是庙会。
庙会是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寺庙广纳四方香火,人流量大,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商贩们在寺庙外摆起摊子,为烧香拜佛的人提供小吃或便餐,兼售各色货物,而后渐渐成为定期活动,称为“庙市”或“庙会”。清代是北京庙会的繁盛期,《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至于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庙市上四方商贩云集,游人如织。
清末和民国年间,政权鼎革,思想激荡,许多寺庙在宗教、政治上的功能废弛消亡,但作为零售经济和文化娱乐的场所反而持久兴盛。护国寺在历史上曾多次因灾受损又重建,至清代晚期再遭火灾时,朝廷已无暇修缮。进入民国后更是兵荒马乱不休,大量建筑破败严重,渐次荒芜,大量闲置出来的空地倒是正好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支布搭棚做买卖的地方。寺庙也需要招商收租来补贴生计,于是佛事不兴商事兴,由于庙会的存在,护国寺作为市民定期聚集活动的公共空间,依旧在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崇国寺到隆善寺再到护国寺,其漫长旅程见证了北京城的朝代变迁与兴衰更替。雕栏玉砌已不在,昔日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只余下一座五间单檐歇山顶的金刚殿,宛如旧时光的纪念碑,静默地栖在水泥围墙之中,怡然自得。护国寺作为寺院的历史已然谢幕,如今化身为广义上的地标,其周边的护国寺街、护国寺小吃等各种以“护国寺”为前缀的处所,是市民与游客的热门去处,延续了这片地段曾有的繁华和热闹,也延续着对国泰民安、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到了清乾隆年间,护国寺前形成了正式庙会,阴历每月初七初八,护国寺街上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大到文物珠宝,小到针头线脑,在这庙会上就没有买不到的。不过,最让人心动的还是那些叫卖小吃的吆喝声,扒糕、切糕、豌豆黄、艾窝窝、豆汁儿、面茶、老豆腐……哪一样都看着透亮闻着飘香。护国寺的庙会已经多年不办,这些小吃去哪儿了呢?
20世纪50年代,政府把小吃摊主组织到一起公私合营,这才有了今天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茶汤英、切糕刘、扒糕年……护国寺小吃店里的每一种知名小吃都有着200年以上的历史。小吃店的店面不算大,但每天人来人往客流不少,喝着烫嘴的豆汁儿,嚼着香脆的焦圈,谙熟老北京的常客和寻觅老北京风情的游人会情不自禁聊起老北京的故事,东西吃完了,故事却还在回味。
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
护国寺街还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从西口进来不远,路南有一座红墙绿瓦的三层仿古建筑,这是专为表演京剧而建的人民剧场。
北京人民剧场始建于1953年,1955年1月正式建成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心下修建的以戏曲表演为主的现代化剧场。与同时期建成的首都剧场和天桥剧场有所不同,北京人民剧场属于中式风格建筑。
自落成以来,梅兰芳等艺术大师、戏剧名家都曾在此登台献艺,留下了几代艺术家的足迹。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来此观看演出。1959年5月25日,梅兰芳先生一生排演的最后一部新戏《穆桂英挂帅》也在此进行了首演。可以说,北京人民剧场是见证新中国戏曲发展史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里程碑,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2007年底,北京人民剧场列入北京市第一批北京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名录,并于2018年列入中国20世纪第三批建筑遗产。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北京人民剧场因存在安全隐患在2003年停业。2011年,北京人民剧场在护国寺大街重新亮相。重建后依然保持了原有历史风貌,但将原剧场观众区至舞台部分全部拆除重建,前厅门脸进行加固大修,重新油漆彩绘。在功能上,北京人民剧场也另辟蹊径,转向京剧文化产品,改造成为数字摄影基地,进军新领域。2016年,北京人民剧场被中宣部确定为“中国京剧音像工程北京拍摄基地”,主要功能定位为数字电影拍摄、剧目合成彩排等。
护国寺街东头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大师生前最后十年就栖居在这座四合院。1986年梅兰芳诞辰92周年之日,梅兰芳纪念馆正式开馆。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61年8月8日,梅兰芳病逝,10日上午,首都各界两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
而今,再次走进梅兰芳故居,不仅能看到复原的客厅、卧室、书房,家居摆设一应俱全,仿佛斯人从未走远。厢房里还有大师穿过的经典戏服,以及大师亲手绘制的花鸟人物画作。走进这院子,即使是对京剧懵然不懂的后生小子也会生出对国粹的敬意。
走进百花深处
来到护国寺街,有几条与之相连的小胡同也值得一逛。“百花深处”在北京的数千条胡同中名字最为雅致,引人遐想。“百花深处”真的很浪漫吗?其实不然。真走进去,才发现这里根本称不上一条正儿八经的胡同,只是一些院落的杂乱组合,大多建筑都是近年所建,而且相对比较简陋,似乎也没什么大宅院或名人故居。
据《北京琐闻录》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一对张姓夫妇在此购地种菜,后叠石为山、掘池种莲,将菜园扩建为园林。夏日荷香里泛舟采莲,秋日菊影中饮酒赋诗,冬日梅雪下围炉煮茶——这座私家园林吸引着京城文人雅士,成为晚明风雅的缩影。“百花深处”这个雅致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清代乾隆年间园林荒废后渐成巷陌,改称“花局胡同”。待到光绪年间,褪色木牌重新镌刻上“百花深处胡同”。民国时又去“胡同”二字,唯留“百花深处”的雅名,沿用至今。
老舍曾这样描述百花深处:“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
从百花深处一拐弯是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他曾在《四世同堂》里详细描述过这条留下童年记忆的小巷。护国寺街北的棉花胡同,也是有故事的地方。大太监李莲英曾在这里买下一座宅院送给继子,现在是护国寺中医医院所在地,民国时的护国大将军蔡锷也在这条胡同住过。
记者付善元整理 姜灏摄
参考资料:
《闲话护国寺:从佛教重地到庙会胜地》栗河冰
《护国寺不仅有小吃,曾经也有寺》李哲
《护国寺与护国寺街古今谈》邸永君
注:
本版信息来源“京报移动传媒数字资料库”
相关作者可联系编辑程林琳
联系方式:17701310781
 如今的护国寺街景
如今的护国寺街景 游客在梅兰芳故居前拍照打卡
游客在梅兰芳故居前拍照打卡 如今的人民剧场
如今的人民剧场 护国寺金刚殿作为市级文保单位仅限外部参观
护国寺金刚殿作为市级文保单位仅限外部参观 护国寺小吃特色必吃榜
护国寺小吃特色必吃榜 护国寺小吃店铺
护国寺小吃店铺 如今的金刚殿外景
如今的金刚殿外景从崇国寺到护国寺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一幅传世作品《崇国寺演公碑》,被赞为“人书俱老,用笔圆润端肃”,是其晚年书碑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碑文内容也是一份重要史料。
《崇国寺演公碑》全称《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立于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由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丹、篆额,记述了护国寺前身崇国寺始创者定演禅师的生平事迹,以及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赐地兴建崇国寺的来龙去脉。这座为后世史书誉为“悉皆完美”的崭新佛寺名曰“崇国寺”,为区别于此前已存在的一座同名寺院,时人呼其为“北崇国寺”或“崇国北寺”。
北崇国寺开创于元代,而崇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清代《日下旧闻考》收录危素的“大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证慧禅师傅戒碑略”中记载了元军攻打金军时“闵忠崇国二寺”俱为兵毁,以及元朝大臣雅克里、耶律楚材等修复两寺的事迹,可知崇国寺在元灭金战争中被毁,嗣后得以重建。而《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赵宋宗室赵子砥《燕云录》记下了靖康之耻时“中书侍郎陈过庭并文武官五十余员”于丁未八月在燕山崇国寺安泊的记录,这意味着崇国寺可能在辽宋时期便已存在。据黄春和先生在《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中考证,隋唐时期幽州城佛寺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可考者达17座,其中便有悯忠寺和金阁寺两座。据《顺天府志》载:“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析津志》中也道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
为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护国寺之名,是逐步演化来的,几乎每修一次,都要改换一次寺名。明宣德四年重建后,由崇国寺改为御赐的大隆善寺,到了明正统四年,重修后又改为崇恩寺。到了33年后的成化八年,由著名的大工匠工部侍郎蒯祥主持重修,赐名大隆善护国寺,这是护国寺其名之始。后经康熙、乾隆、道光历岁重修,护国寺之名未再更改,山门上始终是大隆善护国寺的石额。
护国寺的整体格局,也是逐步形成的。随着逐代的增修,护国寺的纵深越来越夸张,主要是不断增加前端的门户。护国寺天王殿是最早的山门,正统时在其前增建一道山门——金刚殿,到了成化那次重修,又在金刚殿前加了座临街砖石山门,全寺格局才最终形成。
护国寺只门户就有三重之多,三门之后,又有层层递进的三座大殿,而这三门三殿,还只是前院,后院还有一门一殿一坛一楼,由此形成了超长纵深的九进格局,这是元代大寺院的典型特征,前院廊庑围合的特点也是型古而制高,颇有巨刹古风。
值得一提的是前院最后端的千佛殿,这才是最古的殿宇,俗称土坯殿,20世纪30年代寺庙调查时土坯墙坍塌只剩四框,但正是这残存的土坯墙和独特的角石,证明这是一座元代建筑。同时期还有舍利塔、后院门前石狻猊及数通元碑,保存至今的,除石碑外,也只有千佛殿的元代雕花柱础了(一在原址,一在北京钟楼台基东坡道北角)。其余的钟鼓楼、金刚殿、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三大士殿、戒坛以及配殿廊庑都已属明清建筑。
因庙会变得十分热闹
除了以朝廷的香火寺和藏传佛教僧人居住而闻名之外,护国寺更以庙会享誉京城内外。佛寺在古代长期承担着公共空间的角色,同时也是许多地方的文化中心。而建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寺院,不仅在宗教、政治和文化上活跃,又是市民的活动广场与休闲胜地,更承担了十分突出的商业功能,其主要形式之一便是庙会。
庙会是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寺庙广纳四方香火,人流量大,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商贩们在寺庙外摆起摊子,为烧香拜佛的人提供小吃或便餐,兼售各色货物,而后渐渐成为定期活动,称为“庙市”或“庙会”。清代是北京庙会的繁盛期,《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至于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逢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逢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庙市上四方商贩云集,游人如织。
清末和民国年间,政权鼎革,思想激荡,许多寺庙在宗教、政治上的功能废弛消亡,但作为零售经济和文化娱乐的场所反而持久兴盛。护国寺在历史上曾多次因灾受损又重建,至清代晚期再遭火灾时,朝廷已无暇修缮。进入民国后更是兵荒马乱不休,大量建筑破败严重,渐次荒芜,大量闲置出来的空地倒是正好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支布搭棚做买卖的地方。寺庙也需要招商收租来补贴生计,于是佛事不兴商事兴,由于庙会的存在,护国寺作为市民定期聚集活动的公共空间,依旧在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崇国寺到隆善寺再到护国寺,其漫长旅程见证了北京城的朝代变迁与兴衰更替。雕栏玉砌已不在,昔日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只余下一座五间单檐歇山顶的金刚殿,宛如旧时光的纪念碑,静默地栖在水泥围墙之中,怡然自得。护国寺作为寺院的历史已然谢幕,如今化身为广义上的地标,其周边的护国寺街、护国寺小吃等各种以“护国寺”为前缀的处所,是市民与游客的热门去处,延续了这片地段曾有的繁华和热闹,也延续着对国泰民安、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到了清乾隆年间,护国寺前形成了正式庙会,阴历每月初七初八,护国寺街上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大到文物珠宝,小到针头线脑,在这庙会上就没有买不到的。不过,最让人心动的还是那些叫卖小吃的吆喝声,扒糕、切糕、豌豆黄、艾窝窝、豆汁儿、面茶、老豆腐……哪一样都看着透亮闻着飘香。护国寺的庙会已经多年不办,这些小吃去哪儿了呢?
20世纪50年代,政府把小吃摊主组织到一起公私合营,这才有了今天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茶汤英、切糕刘、扒糕年……护国寺小吃店里的每一种知名小吃都有着200年以上的历史。小吃店的店面不算大,但每天人来人往客流不少,喝着烫嘴的豆汁儿,嚼着香脆的焦圈,谙熟老北京的常客和寻觅老北京风情的游人会情不自禁聊起老北京的故事,东西吃完了,故事却还在回味。
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
护国寺街还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从西口进来不远,路南有一座红墙绿瓦的三层仿古建筑,这是专为表演京剧而建的人民剧场。
北京人民剧场始建于1953年,1955年1月正式建成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心下修建的以戏曲表演为主的现代化剧场。与同时期建成的首都剧场和天桥剧场有所不同,北京人民剧场属于中式风格建筑。
自落成以来,梅兰芳等艺术大师、戏剧名家都曾在此登台献艺,留下了几代艺术家的足迹。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来此观看演出。1959年5月25日,梅兰芳先生一生排演的最后一部新戏《穆桂英挂帅》也在此进行了首演。可以说,北京人民剧场是见证新中国戏曲发展史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里程碑,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2007年底,北京人民剧场列入北京市第一批北京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名录,并于2018年列入中国20世纪第三批建筑遗产。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北京人民剧场因存在安全隐患在2003年停业。2011年,北京人民剧场在护国寺大街重新亮相。重建后依然保持了原有历史风貌,但将原剧场观众区至舞台部分全部拆除重建,前厅门脸进行加固大修,重新油漆彩绘。在功能上,北京人民剧场也另辟蹊径,转向京剧文化产品,改造成为数字摄影基地,进军新领域。2016年,北京人民剧场被中宣部确定为“中国京剧音像工程北京拍摄基地”,主要功能定位为数字电影拍摄、剧目合成彩排等。
护国寺街东头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大师生前最后十年就栖居在这座四合院。1986年梅兰芳诞辰92周年之日,梅兰芳纪念馆正式开馆。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61年8月8日,梅兰芳病逝,10日上午,首都各界两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
而今,再次走进梅兰芳故居,不仅能看到复原的客厅、卧室、书房,家居摆设一应俱全,仿佛斯人从未走远。厢房里还有大师穿过的经典戏服,以及大师亲手绘制的花鸟人物画作。走进这院子,即使是对京剧懵然不懂的后生小子也会生出对国粹的敬意。
走进百花深处
来到护国寺街,有几条与之相连的小胡同也值得一逛。“百花深处”在北京的数千条胡同中名字最为雅致,引人遐想。“百花深处”真的很浪漫吗?其实不然。真走进去,才发现这里根本称不上一条正儿八经的胡同,只是一些院落的杂乱组合,大多建筑都是近年所建,而且相对比较简陋,似乎也没什么大宅院或名人故居。
据《北京琐闻录》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一对张姓夫妇在此购地种菜,后叠石为山、掘池种莲,将菜园扩建为园林。夏日荷香里泛舟采莲,秋日菊影中饮酒赋诗,冬日梅雪下围炉煮茶——这座私家园林吸引着京城文人雅士,成为晚明风雅的缩影。“百花深处”这个雅致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清代乾隆年间园林荒废后渐成巷陌,改称“花局胡同”。待到光绪年间,褪色木牌重新镌刻上“百花深处胡同”。民国时又去“胡同”二字,唯留“百花深处”的雅名,沿用至今。
老舍曾这样描述百花深处:“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
从百花深处一拐弯是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他曾在《四世同堂》里详细描述过这条留下童年记忆的小巷。护国寺街北的棉花胡同,也是有故事的地方。大太监李莲英曾在这里买下一座宅院送给继子,现在是护国寺中医医院所在地,民国时的护国大将军蔡锷也在这条胡同住过。
记者付善元整理 姜灏摄
参考资料:
《闲话护国寺:从佛教重地到庙会胜地》栗河冰
《护国寺不仅有小吃,曾经也有寺》李哲
《护国寺与护国寺街古今谈》邸永君
注:
本版信息来源“京报移动传媒数字资料库”
相关作者可联系编辑程林琳
联系方式:17701310781



打开APP阅读全文